编译者:贺承松
【所评书目】AyșeZarakol,Before the West: The Rise and Fall of Eastern World Ord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文献来源】Valerie Hansen,“Old World Order:The Real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Vol.101,No.5,2022,pp.219-225.
【作者简介】
(1)书籍作者:艾莎·扎拉科尔(Ayșe Zarakol),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教授,伊曼纽尔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体系中的东西方关系、世界秩序的历史和未来、现代性和主权的概念化、大国的崛起和衰落,以及比较研究视角下的土耳其政治等。
(2)书评作者: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汉学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丝绸之路史及世界史等,著有《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丝绸之路新史》等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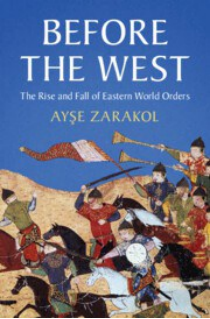
一、《西方之前》概述
现代世界始于何时?国际关系学者们倾向于把他们学科的起源追溯到大约500年前,当时西欧的少数几个国家开始在非洲、亚洲与美洲建立殖民地。在他们看来,由欧洲殖民主义引发的变化造就了今日的世界。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长期不和的欧洲列强签订的这两款和约结束了一系列血腥的战争。因此,有观点认为,这就是国际关系的真正起始点,因为得益于该和约,欧洲各国首次正式同意尊重彼此在已划界领土的主权,为一个被划分为主权民族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世界奠定了基础。
这种欧洲中心的旧历史观仍然塑造着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看待世界的方式。在选择与当今世界事件相关的历史时,他们鲜少能超越1500年以后建立的欧洲世界秩序。他们认为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事件,并且非欧洲国家也不遵守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原则。因此,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诸多历史事实都与理解现代政治基本无关。
然而,只关注欧洲人利用枪炮控制其遇见的各种民族的世界,就会忽略欧洲以外和欧洲所控制殖民地发生的很多事情。若以这种西方主导视角回溯式地解读历史,就会得出这样一种观点,即此前发生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少数欧洲和北美国家的霸权。而最近几十年中国、印度和日本等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恰恰揭示了这种视角和观点的误导性。
在《西方之前》一书中,剑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艾莎·扎拉科尔提出了一种巧妙的方法破解这一智识困境(intellectual impasse)。她以清晰、有力的文笔回顾了早期非西方帝国试图创造世界秩序的经历,这使得书写一种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国际关系新历史成为可能。她的研究揭示了过去世界非西方地区政治相互作用的方式,而正是这种相互作用的方式塑造了这些地区的现代政治领导人对当今国际秩序的理解。
扎拉科尔挑战了现代国际体系肇始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观点。相反,她提出了一种引人深思的替代性方案,即将现代世界秩序的开始追溯到1206年,彼时成吉思汗被誉为欧亚草原所有民族的统治者。扎拉科尔重点关注了由成吉思汗及其多元的继承者们建立的“成吉思汗秩序”(Chinggisid order)。扎拉科尔的观点颇具独创性与新意,但忽略了一些关于蒙古帝国外交的重要原始资料,从而无法更准确地描述蒙古人和他们的后继者是如何在这个新生世界秩序中与邻国的外交官互动的。
扎拉科尔正确地指出了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平行的成吉思汗秩序的重要性。自十三世纪开始,在成吉思汗以及其继承者的统治下,蒙古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其疆域横贯草原,东至匈牙利,西迄中国(译者注:此处作者遵从蒙古的游牧习俗,蒙古人以左为东,以右为西,这与之前的匈奴人以及突厥人习俗一致)。成吉思汗渴望统治整个世界,并在此基础上与邻国建立外交关系。他的继任者都没能控制这么大的领土,但以蒙古人为榜样,他们分别在今天的中国、印度、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明王朝、莫卧儿帝国、萨法维王朝和帖木儿帝国。对如今的现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是,现在生活在原蒙古帝国的各民族充分意识到这一过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野心即是例证。
二、成吉思汗塑造的世界
扎拉科尔将关注点放在蒙古人身上的决定,使她以全新的方法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史惯例。她对亚洲国家政治的兴趣使她并未假定亚洲国家与欧洲国家之间的互动比亚洲国家间的互动更重要。她也没有错误地将早期的亚洲大国仅视为一种区域性大国。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都渴望着统治他们所知的世界。诚然,他们并没有成功(就此而言,也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强国获得成功),但他们领导着由骑兵组成的庞大军队,建立了一个与能与多个邻国和远离欧亚草原的国家进行外交往来的帝国——这也成为后来亚洲国家统治者的长期榜样。
正如扎拉科尔所描述的那样,成吉思汗秩序持续了近500年(比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还要长),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200年到1400年。它既包括最初由成吉思汗统治的统一的蒙古帝国,也包括1260年帝国分裂后的四个继承国,即今天的中国、伊朗、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中亚。三个位于西方继承国的统治者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作为当今中国和蒙古最东端统治者的忽必烈则支持佛教、道教、儒家和其他宗教。这些国家在14世纪的和平共处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开始……当时理性的国家利益胜过宗教信仰。”在这里,扎拉科尔夸大了她的说法:事实是,宗教信仰在当时的政治中经常与“理性的国家利益”交织在一起。统治者选择对哪种宗教或者实际上是哪几种宗教进行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政治盟友的选择。
第二阶段的成吉思汗世界秩序则包含了1336年至1405年“跛子帖木儿”建立的帖木儿帝国和1368年至1644年间中国的明朝。帖木儿以成吉思汗为榜样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甚至娶了成吉思汗的后裔来强调与大汗的联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明朝统治者将所有资源集中在打败各类蒙古和突厥敌人(包括帖木儿的部队)上。即便如此,明朝的皇帝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蒙古陆地帝国的继承人,于是他们派出了一支载有28000人的宝船远至东非,向世界展示他们的力量。尽管对蒙古人的看法有所不同,但帖木儿和明朝早期的皇帝都渴望像成吉思汗一样统治一个庞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帝国。
扎拉科尔提出的第三阶段涵盖了莫卧儿王朝、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的“千禧年君主”(the millennial sovereigns)或“合相君王”(sahibkiran)们(在15-16世纪时期,由于按伊斯兰教历即将接近千禧年,所以出现了一系列基于新千年的谶纬与神秘学说,苏菲派传说会有伟大的马赫迪与圣人降世带领救世。彼时伊斯兰世界的君主积极运用这一谶纬将自身包装成为应世的弥赛亚来巩固王权即成为千禧年的救世主带领国家走向新千年。“合相君王”和伊斯兰的星象占卜有关,伊斯兰占星术认为星象的运转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合相君王”是形象运转到大周转时的君王,是最具神圣属性的君王,承担联合伊斯兰世界的使命——译者注)。由于与蒙古人没有家族关系,这些统治者没有明确地按照成吉思汗的风格行事,但都追求统治世界。他们成功利用骑兵的力量分别征服了现代印度、土耳其和伊朗的大片领土,并与欧洲殖民大国形成真正的竞争。扎拉科尔恰如其分地以这三个王朝在1700年左右的衰落作为本书结尾。
五个世纪中成吉思汗秩序下的国家均有一些共同的关键特征。他们不像一些欧洲大国通过长子继承制选择统治者,而是通过“同宗长者继承”(tanistry)制度。这一术语(借用不列颠群岛凯尔特部落的历史实践)意味着,只有最有资格的个人才能在领导人死后统治该群体。这一制度虽然乍听起来像是民主,但其实完全不同。事实上,这意味着追逐权力的人必须在无节制的暴力中获胜,而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年,直到全体勇士聚在一起为新领袖山呼万岁。蒙古人相信是上天(或宇宙)在继承者争斗中选择了最终的胜利者。为了更好地理解上天的意图,成吉思汗秩序的统治者邀请外国天文学家访问他们的宫廷,并花大笔资金用于建造大型天文台。
扎拉科尔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成吉思汗秩序下的统治者们有同样的“对全世界的特殊愿景”,并创造、修改和复制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历史学家对这一阶段的政治和制度史的细节很感兴趣,而扎拉科尔则将此纳入国际关系学者的视野。在此过程中,她的视野超越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观,特别关注了那些曾经屹立于现代中国、印度、伊朗、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土上的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渴望建立与蒙古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帝国。她超越了局限于单一国家、种族或宗教的历史叙事框架,解释了亚洲各国统治者如何互动并在此过程中创建了可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相媲美的外交体系。
三、毛毡靴子和金属护照
五个世纪是很长的时间跨度。《西方之前》的第一部分回顾了多个王朝的重大事件,解释了它们为什么被认为符合(或不符合)成吉思汗秩序。本书最明显的问题是有关研究主题即“外交”的材料的缺乏。这一不足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已有两份广为流传的对成吉思汗秩序下统治者进行外交访问详细记载的英文资料。这些记载描述了成吉思汗外交秩序的实际运作情况,但却与扎拉科尔对蒙古人统治效率的乐观主张恰好相反。
1253年至1255年间,比利时方济会修士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前往今蒙古哈拉和林附近,觐见成吉思汗之孙蒙哥(Mongke)的汗廷。法国十字军国王路易九世派遣鲁布鲁克作为传教士(而非特使)前往蒙古,但当他抵达黑海的索尔代亚港(Soldaia)时,蒙古汗廷却从当地商人那里听说他是一名外交官。因此,鲁布鲁克决定接受使者的特权,没有尝试解释传教的愿望。像所有方济会修士一样,他身着棕色长袍,赤脚而行,这给他穿越寒冷草原的旅程带来了巨大困难(最终他屈服了,穿上了毛皮大衣和毛毡靴)。尽管没有50年后的《马可波罗行纪》那么出名,鲁布鲁克的记载仍在1990年彼得·杰克逊的译作中占据近300页的位置。他记载提供了目前关于蒙古帝国最敏锐、最详尽的描述。作为一名细心的观察者,鲁布鲁克为其赞助人路易九世撰写了一份严谨的报告。他在描绘蒙古人时写道,“我来到他们中间时,真觉得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的描述准确地展现了蒙古人如何对待进入他们领地的外交官。
在1253年7月,当鲁布鲁克抵达成吉思汗的曾孙班秃(batu)的宫廷后,他请求获取在蒙古地区传教的官方许可权[彼时基督教分支——东方亚述教会(the Church of the East)已在当地开展了传教活动],但班秃将鲁布鲁克送到了他的父亲蒙哥大汗的首都哈拉和林,因此,鲁布鲁克推测,班秃作为一名地区领导人,虽然他能处理与自己管辖范围有关的所有事务,但不得不将诸如传教等国际外交事务交给大汗。由此可见,扎拉科尔夸大了成吉思汗式统治的效率:因为只有可汗才能在某些问题上做出决策,如果他不在,没有人可以替他做决定。鲁布鲁克抵达了蒙哥汗在今蒙古国翁金河的冬季行宫,他通过一个翻译向大汗表达了传教的请求,但由于翻译和大汗都喝醉了,因而没有得到明确答复。起初鲁布鲁克被允许在汗廷待两个月,但他在行宫待了三年之后又在蒙古首都哈拉和林待了三年,并在那里参与了一场穆斯林、佛教徒和其他基督徒的宗教辩论。但辩论并没有定论,鲁布鲁克最终在没有得到在蒙古帝国领土传教的情况下离开了那里。
鲁布鲁克的记载揭示了蒙古人统治的事实,即蒙古统治者们可能有建立一个世界秩序的雄心壮志,尽管存在着高效的驿站系统可以让信息和鲁布鲁克这样的旅行者穿越帝国,但帝国本身仍然是高度分散的。大汗并不能直接统治他的帝国,相反,他任命了一批地方官员进行自治,这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在蒙古人崛起之前当地政权的管理方式。
大约150年后,一名西班牙外交官也与鲁布鲁克有着相似的经历。1404年,卡斯蒂利亚国王亨利三世试图与蒙古帝国结盟以对抗奥斯曼帝国,因此派遣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Ruy González deClavijo)前往撒马尔罕(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重要贸易中心)觐见帖木儿。帖木儿帝国首都的奢华给克拉维约留下了深刻印象。帖木儿慷慨地接待了克拉维约及其随从,为其提供了充足的酒肉,还多次邀他们参加宴会。但当帖木儿染疾后,他的三名顾问接手了国事。因为无法行使实际权力,他们敦促克拉维约踏上归途。但克拉维约拒绝了,因为他的任务是获得帖木儿给亨利三世的回应。但是到达两个月后,克拉维约无功而返,结果陷入了帖木儿帝国各势力为接管帝国所爆发的冲突中。克拉维约的经历与鲁布鲁克类似:可汗是唯一能决定帝国外交关系的人。
扎拉科尔认为成吉思汗“通过自己的榜样传播了政治统治者作为唯一最高权威的规范,并通过全球统治将之合法化”。她声称,成吉思汗引入了“极高度的政治集权……将所有相互竞争形式的权力都收归于己”。可汗有权领导军事行动,用掠夺的财物奖励追随者。但在和平时期,可汗的权力要小得多。扎拉科尔的观点显然与鲁布鲁克和克拉维约的经历并不一致,即可汗保持着“最高权威”,只有他才有权决定特定事务,比如允许方济会修士传教或给另一位统治者回信,但他从未采取真正整合帝国不同部分的政策。
四、其他中心、其余世界
学者们可以就过去的某一特定解释是否准确进行争论,但对过去的一般理解(特别是决策者对过去的理解)往往会塑造现代国际关系。正如扎拉科尔所建议的,学者们需要对她的作品涵盖的时期发问:“那个时代运作的逻辑中,哪些在我们的时代仍然起作用?”她的最后一章探讨了欧亚主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运动,确立了横跨欧洲和亚洲的非欧洲世界秩序先例),更具体地说,是日本、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如何理解蒙古统治对自身社会的长期影响。这一对欧亚主义的关注可谓及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俄罗斯学者如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Nikolai Trubetzkoy)、乔治·维纳斯基(George Vernadsky)和列夫·古米廖夫(Lev Gumilyov)等一直在争论长达两个世纪的蒙古统治对现代俄罗斯的影响。他们呼吁俄罗斯的现代领导人效仿成吉思汗,统一俄罗斯以建立横跨欧亚的新帝国。苏联解体后,这种思想非常受欢迎,普京也经常被比作成吉思汗。普京的顾问们并不关心历史准确性。在为欧亚主义以及它怎样给俄罗斯赋权进行论证时,他们援引了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无关的传统。扎拉科尔的观点很中肯:欧亚主义背后的历史有助于理解曾由蒙古人统治的土地上发生的事件。
与其他真正具有开创性的书一样,《西方之前》涵盖了如此多的新领域,以至于没搞清楚所有的细节(特别是它夸大了蒙古帝国的集中权力)。尽管如此,扎拉科尔还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展示了1500年之前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是如何影响现在和未来的。然而从1206年开始的叙事可能会忽视更早事件的重要性。比如大约在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帝(普京同名)皈依东正教,并定都基辅。当前的事实显示,俄罗斯总统建立新欧亚帝国的雄心正试图将形成于10世纪末的俄罗斯东正教中心地带纳入其中。
这正是扎拉科尔的观点:对1500年前欧洲以外那些试图建立世界秩序的社会进行研究,能揭示现代世界的许多情况。欧洲以外的早期统治者们建立的世界秩序仍然具有深刻意义,因为今天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仍会回忆起过去的功绩和制度,有时甚至试图重建这些制度。关注早期统治者(包括成吉思汗继任者)施行的外交实践,给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一家独大的观点提供了宝贵的平衡。在当今这个多极世界中,美国领导人们每天都在考虑安卡拉、北京、莫斯科、新德里和东京等国领袖的下一步行动,然而,他们很少思考这些地区的历史。或许现在是时候让更多人跟随扎拉科尔的脚步,研究欧洲以外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过去了。
【编译者简介】

贺承松,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国际政治本科生。主持国家级创新创业项目一项,校级创新创业项目三项。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
有恒·欧亚学术团队
为了解学术前沿,开阔学术视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以研究生“笃研”读书会为依托,组建“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团队主要负责编译俄罗斯、中亚、南亚和高加索等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的外文文献,包括学术期刊论文、书评、地区热点及重大事件的相关时评等。自组建以来,编译团队已推出170多期编译作品。现有编译人员30多名,主体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实行组稿与自由投稿相结合的方式。欢迎校内外对欧亚问题感兴趣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投稿,投稿邮箱:zhouwj21@lzu.edu.cn。编译作品将在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同步刊出,一经采用并发布,即奉上稿酬,以致谢意。敬请各位同仁关注、批评与指正。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仅供专业学习之用,相关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贺承松
校对:陈明霞
审校:王术森